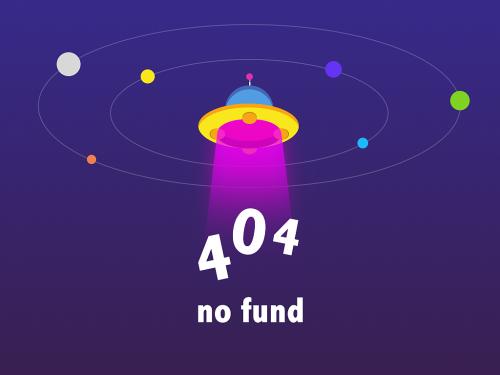在陕北,无论红白喜事还是庙会秧歌,都会请吹手,也就是我们说的唢呐人。陕北唢呐起源于元代,后来经过不断升级和发展,被称为大吹,明代已被民间广泛流传。
在我的家乡也有一班吹手,十里八乡只要说起吹手,肯定有我们村那一班吹手的一席之地。现在村里的人每每坐下来聊天畅谈的时候,总会多少提一句我们村的那班吹手,不为别的,就为唤起属于那个年代却在如今即将消失的记忆。
提起那班吹手,必须要提到的一个人就是贺引民,这个人是领头,更是在唢呐方面很有特长的一个老师傅。我不知道他的唢呐是和谁学的,但我知道他带出来好几个徒弟。那几个徒弟后来也都是十里八乡独当一面的唢呐人。据说贺老先生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吹唢呐,吹了几十年,前几年因病走了,村里的一代唢呐师傅就这么悄悄地离开了。但是他吹奏唢呐的声音依然在我们的耳边回响,久不散去。我觉得贺老先生的唢呐很独特,他在唢呐方面的功夫也是下的很足,尤其是换气高音功夫很是见长。
贺老先生既是一位好的演奏者也是一位乐器整修高手。唢呐这件非常民间的乐器,各个部件的搭配和修整是他必须做的一件事情。小时候曾见过一次他亲手制作哨片,用的是家乡野地里生长的芦草根。把芦草根拔回来以后经过水泡浸润、抽出内杆、铜丝捆扎、砖石打磨等多道工序后方能制成一只像样的哨片。哨片也分为软硬两种,哨片越硬,唢呐吹出来的音量和穿透力就越高,但硬哨片的吹奏是需要极高嘴上功夫和气息功夫的。如果嘴上功夫和气息功夫没有修炼到,那就谈不上唢呐起高音了。贺老先生作为一个十里八乡的唢呐吹奏高手,那些技巧功夫是没得说的,有什么样的曲牌就会吹出什么样的唢呐音,毫不含糊。
小时候村里但凡谁家办事,请的全是村里贺老先生这班吹手,我们一群小孩则是他们的忠实粉丝,除了吃饭时间几乎都围在吹手四周,听他们吹打。
各家的红白事务首先是定日子,其次就是请吹手。到了办事的日子,要吹手吹出响声,事务才算正式启动了。要是在夏天,一般吹手会在阴凉地围成一圈,唢呐在正位,然后才是鼓、镲、锣等各种乐器。除了唢呐,其他几样没有固定的位置。等一班吹手摆开阵势,贺老先生会把夹在腋下的长筒唢呐放在地上,将别在耳朵里的哨片拿出来噙在嘴里,用口水给哨片稍作软化,然后拿起唢呐将哨片安装在唢呐顶端,吹气试音,一股悠扬的特殊陕北唢呐音便响彻天空。待试音完毕以后,其他乐器也调试完成,他示意鼓匠起鼓,后续镲锣相继跟上,一曲唢呐终是来临。假如主家办的是娶妻嫁女等红事,那么唢呐声中尽是喜庆,一曲《得胜回营》将喜庆的气氛一下就推向高峰,高亢优美的唢呐声,伴随着炮仗声,响彻村庄的每一道沟岔梁峁,回荡在村庄的上空。主家听了自然脸上笑容满面,心里想着儿女婚姻美满,生活幸福。如果主家办的事丧事,那么唢呐声中尽是悲哀,一曲《大行礼》让人肝肠寸断,主家一听嗓子里一堵,能够想到父母亲含辛茹苦的那些艰难年月,躲在角落暗自抹两把眼泪。要是事务在冬天,那么吹手就要垒一座用大块炭搭建的火塔。他们围在火塔周围,我们一群小孩更是跟着围在四周,一边听唢呐,一遍烤火,在享受一场听觉盛宴的同时浑身暖暖的。
那时候,总有人在听过贺老先生的唢呐以后说他吹的很不错,可以当很多人的师傅了。但是他总是摆摆手笑着说:我吹的很一般,但是我永远不会胡乱吹打,唢呐这个东西看起来简单其实还是需要点真功夫的,比我好的大有人在,咱们不能这么说。这也是为什么家乡周边好多村子都请他吹唢呐的原因吧。
虽然我们现在都注重创新,但是我认为,现在的这些所谓的创新唢呐吹法太过于肤浅,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唢呐。现在很多唢呐都是那种小唢呐,短筒,声音尖锐,这种短小的唢呐根本吹不出陕北长筒唢呐那种浑厚悠扬的韵味,吹不出陕北人那的性格,反而让人听了很是聒噪,心里总是感觉毛毛的。他们不愿意吹大唢呐吗?不是的,那是他们学不会大唢呐,小唢呐是电子琴的标配,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不符合厚重的陕北大地,不符合气势强大、厚重直爽陕北人。陕北的大唢呐那是扎根民间,来源于本土的非物质文化中的一绝。
家乡的唢呐音是从灵魂深处发出的,每一个音调都充斥着乡村的风霜雨雪,更包含着贺老先生对唢呐艺术的独特贡献。那悠扬的水锣音和着高亢的唢呐声,随着时而急切时而稳定的鼓点,一次又一次在我的耳边回响。在这样的唢呐声里,让逝者安息,生者奋斗,陕北的乡村里上演着十分美妙的生命轮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