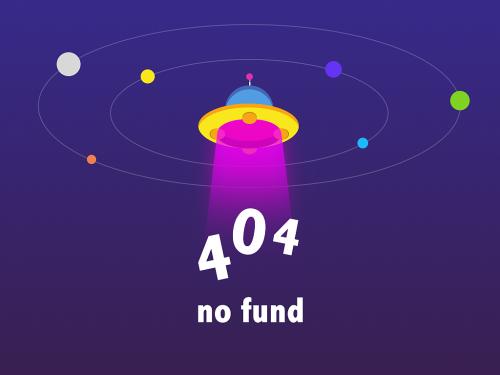近些时日,由于着手重修家谱的缘故,总能想起关于故乡的很多事情。那一口至今只剩一个泉眼的老井总是出现在我脑海里,唤醒我对她的刻骨记忆。
老井处在村子最低的一处不高的崖畔之下,紧挨阴塔蔬菜园子,一条路在她旁边经过。那口老井,历史悠远,据说有了村庄就有了那口井;因无村史记载,其年纪便无从考究。那口老井,曾供给和保证了碾道弯贺王杨三姓祖辈多年的吃水,理当是延续生命的甘甜乳汁。
记忆中,老井在天气不是很干旱季节还能冒出来少许的水,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一小洼清水。水少的另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老井的泉眼在离地面1米多高的石头缝里,就这1米多的距离会把本来少的可怜的水蒸发的更少了。老井在一处悬崖下,那里至今还放着一些柴,都是住在周围的人家为了下雨天能够有干柴烧而储存在那里的。就是经历再多的风雨,柴依然干,老井依然静卧在那里。
现在那眼泉眼在雨季依然生长青苔的老井,见证着全村的从古到今,由小到大。她见证了往昔的穷困贫瘠,也见证了当今的富有丰裕,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由于地下水位下降,老水井已经像一只枯老的眼睛再也不能流泪了。当时,由住在靠近水井边的几位叔叔忍痛割爱,把老井的井沿用铁锹豁开,规整的和路齐平,老水井至此完成了她的使命。
故乡那口老井,映照着全村人的淳朴生活。早上,井边是热闹的,男女老少,在老井旁担水的乡亲们干脆搁下水桶,把扁担架在两只水桶上就成了一把现成的凳子,家长里短,谈天说地;天气炎热的下午,耕种在老井边的一些蔬菜需要浇水,老井旁便更热闹了,男人打水,女人浇地,孩子们光着身子跑来跑去;一派淳朴悠然的农村生活场面。
一到晚上,老井便静怡、神秘了。退去了白天的喧嚣,深邃的她也该歇息了,但她的歇息借着夜色暗黑而神秘,有时又隐藏着恐惧和可怕,不光对小孩,似乎也对大人们。这可能也是全村人都对它亲切依赖而又敬畏无比的原因所在。对孩子们来说,老井即是心系之地,又是嬉戏禁地。家人们时时严加看管,不敢让自家孩子做出一点对老井不敬的事来。大人们更讲些井中有仙、井中闹鬼等可怕故事,吓得孩子们只有望而却步,近而生畏了。
故乡那口老井,曾在村人们的记忆中,是家园,是生命。虽不抵唐朝诗人张籍在《楚妃怨》中描述的那口井“梧桐叶下黄金井,横架辘轳牵素绠”那样高雅;也不抵他在《山中赠日南僧》诗中“独向双峰老,松门闭两崖。翻经上蕉叶,挂衲落藤花。甃石新开井,穿林自种茶。时逢海南客,蛮语问谁家。”的那样归朴悠然;但在村人的记忆中,她也是春有槐花飘香,彩蝶飞舞;夏有浓荫匝照,蛙鸣虫叫;秋有落叶铺地,蛐蛐欢跳;冬有白雪覆盖,麻雀欢跃,是那样富有诗意和情趣。
故乡那口老井,见证着全村人的喜怒哀乐,悲欢离合。当年,每家迎娶出嫁,都要到经过老井,每家也会在老井旁边遮一块红布,祈求儿女婚后幸福源远流长;喜得贵子后,更要端一盆井水为小孩沐浴,祈求平安聪慧。如果遇到旱灾,村中老者带领全村人背着龙王爷淘井祈雨,有时候也颇为灵验。当然,也有周边邻居因家庭恩怨在井边担水浇水的时候互相痛骂几声,更多的却是在同饮一口水的情缘里最终慢慢化解恩怨,老井在这里承担的更是一份老者的说和责任。
故乡那口老井,在她退役近四十多年后,已少有人看望和问津,更有年轻人已不知她的存在,她的功绩,她一直在忍耐和沉默着。
前些时日,我因母亲过世回村,清早挨家挨户磕头的时候经过老井,她依然静卧在那里,仅剩一眼黢黑的泉眼,丝毫没有往日的生机与荣光。故乡那口老井,在我心中,她更是诗,更是画;用槐花写就的诗,用麻雀羽毛绘出的画,也是终生抹不去的化石般记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