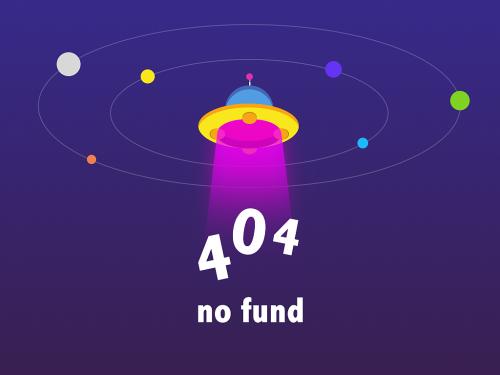上次回乡赶村里的庙会,天降小雨,喜欢雨中漫步的我一个人在村里走了走,看了看我小时候经常去玩耍的地方。当我走到碾道弯的时候,不由得停下脚步,那躺在杂草丛中的石碾是那么的熟悉却又陌生。它像一个经年不见人的老者,沉默无言却又有太多的话想对世人诉说。
碾道弯是村里的一个地名,因有两座石碾且是窝风的半弧形地形而得名。
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农村的孩子应该都见过石碾。用石头砌成圆形台,上面铺一层最细的石头,最中间栽木头桩,然后用整块石头削成圆柱形中间打洞穿木椽,固定在中间的木头桩子上就能用了。
小时候听父亲说石碾是由一条青龙变的,我们要敬畏它。因此,村里人做红白喜事的时候经过石碾,主家就要用一块红布将它盖上,担心冲撞了青龙。每逢春节,村里人都会在石碾中间的木桩上粘贴横写的“青龙大吉”四个大字,以避邪除灾。
冬至前后,是石碾最忙的时候,家家户户都上碾子来碾压自己的收成。将躬耕所收获的粮食碾成下锅的米面。每年这个时候,我都会跟着母亲去碾米面。母亲将石碾套上黄牛,用围裙将牛眼睛遮住,牛就一直转着圈圈拉着碾子向前走,石碾在转动时木头桩子和中间那根木椽摩擦下发出“咯吱”“咯吱”的声响,像一首古老但并没有远去的歌谣。此时,母亲也忙碌起来,一边跟在石碾后面将碾在边上的米用笤帚扫进去,一边还要用簸箕簸,然后用箩子箩,将碾好的细面箩在笸箩里,再将没有碾细的面倒在石碾上继续碾压。母亲头上裹头巾,全身蒙一层薄薄的面粉,这面粉恰好能遮盖她因春种、夏耘、秋收中留在脸上的黝黑,再加上她娴熟、优美的簸、箩等动作,确是好看。小时候的我非常调皮,老是跑去捣乱,母亲挥手一掌过来就是一个白印。母亲在嗔怒中现出笑容,我带着身上的白印笑着跑开了。总之,在石碾旁劳动的每一家人,都是那么快乐。
碾道弯往往是村里人集会的场所。冬季农忙结束,村里人给各自的牛羊喂了草料以后,就来到碾道弯晒太阳,聊收成,聊子孙,聊家长里短。村中长者可坐在碾盘边,而像我们这种小孩子只能圪蹴在旁边或者干脆坐在黄土地上。
我们的的悲喜愁苦都被碾子听过、见过、碾过。它虽然无法用语言来与那些勤劳的乡亲们交流,但那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滚动给村里人带来了最纯净的养命口粮。
时光荏苒,岁月不歇。随着农村生产、生活条件的改善,村里已用上了电磨,石碾子的使用功能渐为削弱。现在,村里的一些老人还喜欢用石碾子,不知是习惯使然,还是情感使然。总之,他们认为只有石碾子压出的五谷才能保持粮食的原味,其中的科学依据大概得由营养学家来提供了。
如今,石碾子的声音依然在我的耳旁回响,石碾所碾压出来的米面的味道是那么的厚重。淳朴老实的父辈们就像这石碾一样,他们用这种最传统的生存方式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。(王勇)